《餘生》 作者:舞鶴
麥田出版社/當代小說家系列 2000年1月初版
要怎麼來說舞鶴的《餘生》呢?我思索良久,一度想要放棄充滿蕪雜敘述與糾結冥想的這本書,太難了。
首先要讀懂舞鶴怪異的語法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舞鶴堅持他的文字美學,從《拾骨》(春暉出版社)、《十七歲之海》、《思索阿邦‧卡露斯》(元尊文化出版)幾本中、短篇小說即開始,不管是刻意拉長轉折的句法還是動、名詞互相轉注假借的顛覆/跳脫,都讓讀者在閱書之際感到痛不欲生!然而也就因為這種閱讀上的顛躓,使得他的小說富含著奇異的美感和挑戰性,讓人深陷其中無法自拔。
楊照在解讀舞鶴的小說時引了王文興《家變》新版序中的一段話:
理想的讀者應該像一個理想的古典樂聽眾,不放過每一個音符(文字),
甚至休止符(標點符號)。【中略…】作者可能是世界上最屬「橫征暴歛」 的人。
舞鶴的小說對於讀者而言,就是那樣「橫征暴歛」的表現。
我且記得電影『入侵腦細胞』(The Cell)裡,心理治療師為了探究病患的心結,在高科技儀器的輔助之下進入病患的潛意識之中,解謎之必須即是以與病患的思考模式進行探索,循著他人的邏輯亦步亦趨、如履薄冰地前行;暴烈的病患可能在腦中不費吹灰之力讓你經歷最殘忍狂亂的想像使你崩潰,那是意識的強暴。你選擇了進入,便只能承受它所帶來的痛楚或快感,你被主觀地操控,直到故事結束為止。
要進入舞鶴的世界也是如此,不管他述說的是什麼樣的主題,你都必須依著他的步調隨之起舞,《餘生》尤其發展大備,他所擅長的客觀書寫和主觀囈語交錯混雜織成一張花樣複麗的大網,全書毫無章節——因為壓根兒連段落都沒有!
而他的小說主角通常很像朱天文筆下的「荒人」,甚至更「荒」一點什麼都不做,他們只是觀看、紀錄、思索。
而《餘生》的觀看主題,是幾乎被蔓草湮滅的「霧社事件」。
「霧社事件」發生在1931年,學者研究事件的原因在於泰雅族賽德克人不滿日據時代「皇民化」統治下的欺壓,近因則是「和蕃事件」和「敬酒事件」的風波。
日據時期,駐台日軍政府為達治理並同化原住民的目的,在高壓統治之外,強迫原住民與日本人通婚,稱為「和蕃」,而當時馬赫坡社群首領莫那‧魯道之妹狄瓦絲‧魯道,也在和蕃之列,狄瓦絲婚後與日籍丈夫相處不睦,便以埋下事件發生之隱因;日後又有賽德克達雅族人婚宴,莫那‧魯道長子達歐‧魯道因向日本軍官敬酒無故被毆,更造成雙方情勢雪上加霜,莫那魯道因此糾集奇萊山區日6個社群參與抗日,襲擊霧社國小,第一次屠殺在1931年10月27日凌晨,136位日本人遭到殺害,是為「第一次霧社事件」。
「第一次霧社事件」造成全台震驚,駐台日軍鎮壓其稱之為「兇蕃」、「反抗蕃」的抗日原住民未果,不惜以正規軍隊加上飛機大砲轟炸,又逼迫以道澤社群為主的泰雅族人組成「味方蕃」(意即「親日者」),以賞金模式鼓勵出草,造成日後以馬赫坡為主的6個抗日主要社群與道澤社群的不合,而在「第一次霧社事件」其間互相出草,使道澤社群損失多名頭目,此間的仇恨埋下了「第二次霧社事件」的前因。
「第一次霧社事件」為期約2個月(10.27~12.30),參與抗日的6個社群共計約1236人,被殺害及自縊者約有644人,其餘生還者561人被俘後被稱為「保護蕃」,安置於「保護蕃收容所」,同年12月30日,日方「諭告」霧社事件結束。
然而日軍久攻不下的恥辱未雪,加之以在「第一次霧社事件」中,與莫那魯道等人征戰而被草去頭目首級的道澤社群族人們,獲得日軍延遲繳交槍銃蕃刀的「默許」,於隔年(1932年)4月25日凌晨,大舉襲擊「保護蕃收容所」,傷殘老弱身無寸鐵的「保護蕃」死亡約216人,其中101人被草了頭顱並拍照存證,是為「第二次霧社事件」。
從小課本和「正統」的歷史研究者這樣告訴我們,「霧社事件」是愛國主義的「抗日行動」、莫那魯道是「民族英雄」;「愛國」和「英雄」是兩張簡單易懂的標籤,我們就「喔~」的一聲不加思索地記下了,對於「霧社事件」的真相及原貌,再也沒有多看一眼…
直到那一天我開始看《餘生》,跟著舞鶴(還是荒人記錄者觀察者「我」)進入倖存的賽德克人所遷居的川中島,才開始逆溯「事件」,並觀看「餘生」。
「餘生」的「餘」在此有兩層涵意,多「餘」或殘「餘」。前者冗贅,後者不足,卻都暗示歷史、社群,或個人主體的缺憾(《餘生》序論:拾骨者舞鶴/王德威)。而在觀看者舞鶴眼中,川中島的居民們幾乎同時懷抱著這兩種缺憾,在「事件」過後以一種「不得不」的方式,存活下來。
所謂「不得不」不見得是委屈,但至少包含了種種的遷就。事件後賽德克人從高山險嶺間被迫遷居至群山環繞、平原地形的的川中島,是一種「不得不」;因環境(地理上及政治上的)變遷,被迫改變狩獵的天性從事農耕生活甚或下山入城以致於思想行為日漸「都市化」忘卻自身的傳統,也是一種「不得不」;昔日的馬赫坡變成觀光勝地「廬山」,也是。當年馬赫坡人退入深山叢林所經過的步道,沒有任何「歷史的標示」只有到處標示「此去可水煮蛋」,彷彿於今這步道只為了「水煮蛋」而存在(p.62)…
觀看著「不得不」的餘生,舞鶴書寫算是自抑且節制的。他並沒有將之淋上腥羶的狗血,讓故事變成一齣齣難堪的獨幕劇;甚至在聽見自稱莫那魯道孫女的「姑娘」述說某次城市賣身經驗,一位五十餘歲的商人細細撫摸過姑娘高山峻嶺的五官與大奶之後,淡淡地說了一句:「祖先在霧社流了那麼多血,想不到,子孫在飯店床上賣」(p.149),之後。
(哇哩咧這要換了別人可以寫出一篇好爛的「清純少女墮入火坑」的小說情節!)
或許是因為不管稱之為「山胞」還是「原住民」還是以九族分類名為「賽德克人」的這些事件餘族,不需要任何煽情的憐憫吧?!歷史是一回事,生活又是另一回事。他們不需要被定位。
舞鶴尋尋覓覓,泅泳在小雜鍋香檳啤酒伯朗米酒裡翻找,企圖為事件「除魅」,袪除其間的政治性及神話性,還原事件的原貌。
然而大多數族人幾乎不願再提起事件。刻意的遺忘是一個原因,事件當時遺存下來的長老們也厭煩了不管哪裡來的學者專家老是到處追問事件當初。但撇開學術框架的界定和歷史令人窒息的霉味,山清水明的川中島居民果真沒受到「事件」的任何影響嗎?在他們眼中的「事件」到底是什麼呢?
事件的本質究竟是文明解釋下「原始性的屠殺」、政府教材裡附會的「政治性的抗暴」,還是泰雅賽德克人民心中「單純的出草」?如果莫那魯道發起事件是為了維護「尊嚴的完整」,則,尊嚴的「正當性」存在嗎?
賽德克道澤人達那夫從根本否認「事件」的歷史存在。達那夫的父親在晚年談及當時,仍無法忘懷當初偷襲「保護蕃收容所」時,割下大量馬赫坡人頭時的激動和喜悅,同理可證,相同的喜悅勢必也存在於割下道澤人頭目17人的馬赫坡人心中。
因此道澤人認為從來就沒有所謂的「霧社事件」,只有「霧社大型出草儀式」,儀式的主持人正好是莫那魯道、出草的對象是日軍,這樣簡單明瞭。「我們的祖靈會認同莫那魯道的出草儀式,但不會理會什麼霧社事件—」(p.46)
而在村中第一高學歷巴幹眼中,卻明白地表示「事件」與「政治性」的密不可分:「出草是霧社事件的手段但不是動機也不是目的,動機和目的都是『政治性的』,莫那魯道發起霧社事件並不是為了出草,而是政治性的反抗期望求得政治性的正義,事件中大量出現的出草行為,因為那是傳統的、正當的手段,所以以『出草』來否定事件的『政治性』,那是一種扭曲了事實的研究,」「歷史評論者可以在『事件』後充分討論適切與否,但她們永遠不能回到歷史的現場去感受、分析、判斷並做決定,我尊重莫那魯道的決定,也許付出的代價太高,但我還是維護莫那魯道的決定,他站在『現場』判斷並做了決定。」(p.188~189)
好吧,在我被繞口令弄昏之前大概有以上的結論:莫那魯道的決定不能以正確不正確論之,同樣的,霧社事件也不能單一化地與政治反抗劃上等號。出草是一種「行為」,但非動機或目的(如巴幹所說),原因摻雜了維護尊嚴的正義以及出草儀式本身巨大的喜悅等等,但即使是尊嚴受損,非得演成一連串的屠殺連續劇嗎?舞鶴跟我有同樣的疑問。
舞鶴以為「屠殺的不義」可以對決一切包括「反抗的尊嚴」和「出草的儀式」,並試圖論述這「尊嚴的正當性」:『我可以接受事件的遠因和近因,同時意識到遠近都牽連到「尊嚴的完整」,但是人生現實,受損受剝奪了的尊嚴的現象一直存在,人必要為了受剝奪的,即使像尊嚴這樣的東西而以身相殉嗎?我不贊同,當代也質疑它的正當性。只因為「存有比尊嚴正當」,存有在所有存在之先』(p.102)
話說川中島有位怪叔叔叫做宮本先生,小時接受日式教育到小學高等科,就充分體會了大和民族的武士精神是生命的精髓。宮本家中放著一個空武士刀架,修習著他自己的「武士禪」。那日舞鶴請教宮本「武士的尊嚴」,宮本引了武士道的祖師爺宮本武藏的故事為例,說:「平常武士有無上的尊嚴,真正的武士到最後了無尊嚴,」「尊嚴只是暫時,太過於注重或強調它就會誤用了它,面對優勢強權,尊嚴稍作屈身其實是對『實際』屈身,並沒有失去尊嚴,莫那魯道只需如此就可以度過,無須事件。」(p.128)
所以?所以「尊嚴」是「事件」真正的起因嗎?我寧可相信「尊嚴」是莫那魯道當時一個隱性的發想,畢竟「捍衛民族/個人尊嚴」這種呼口號般的事,只有在唐吉軻德的世界和小學教科書裡會出現。在賽德克人不管是發起屠殺的馬赫坡社群人還是後來展開偷襲二度引起屠殺的道澤社群人觀念中,他們藉由「出草」肯定了「事件」,再由「事件」肯定了「屠殺」,名稱雖有不同,但殺戮的本質是一致的。倘若為了維護尊嚴造成殺戮導致族群幾近滅絕,莫那魯道當初若可預見族人這樣的「餘生」,他會義無反顧地再次發動「事件」嗎?
事件的前一夜,莫那魯道都想了些什麼?他在山嵐間呼吸著夜霧時,祖靈向他耳語了嗎?
餘生裡的族人們再也沒有機會感受出草的狂喜和悸動,「出草」與「黥面」再過一代,怕只能成為神話在稗官野史之間傳唱,再也無人知曉其中的奧義…
值得拍手的是,撇開事件嚴肅的議題和歷史的懸疑單看出草行為,舞鶴寫「出草」的幾段都十分引人入勝,演譯之下,「出草」與「性」似乎產生了密不可分的關係。
道澤群人達那夫曾詢問年邁的父親,老父親文不對題地懷想起第二次事件,兩上出現極其甜蜜迷惘的表情…那滋味說不得的!我私心揣想密謀與埋伏,等待的喜悅與割下頭顱的至福充盈之感,似乎也與性愛高潮相去不遠。每一回的出草對獵人而言都是一場的盛宴,那是對獵人獵性的再提昇、近乎對自我的激勵及追求完整,展現獵人大無畏的勇氣—也對獵人頭都不怕了天地有啥可以懼怖?
大獵人是族中的英雄,泰雅少年從小仰望著英雄,仰望著被草下的高懸的頭顱,揉合了無明的恐懼和瀰漫危險氣味的刺激讓他們更形剽悍,不同社群間的族中互草層出不窮,一切都是為了成就「英雄」兩字,這就是族人們追求的理想境界了。而經歷過追逐、戰鬥、廝殺之後,幾乎與山河同步脈動的「獵首祭」的癲狂歡慶,刺激了男人女人的性慾在那之後可以春藥似地維持高漲的衝刺動力與飽滿的幸福感好幾週,這被草下頭顱不論是誰,竟神奇地經由「出草儀式」如同「淨靈」般地化卻仇怨,成為「愛人」。
「愛人頭顱」可能被擺在窗櫺上睜著眼,見證了力如高山崩洪般的性交,第二天獵人開始與「愛人頭顱」的親密交心,首先以豐盛的酒食歡迎愛人來此作客,而後每一天他都有功課要做;今天挖下愛人的眼珠明天開始拔除愛人的頭髮可能要持續好多日,愛人開始腐爛了要埋在秘密之地還是選塊溪石慢慢磨去愛人的臉皮,他都要跟愛人絮絮商議。獵人與愛人頭顱間的私密情誼就在每日的對話自語間完成,凡此兩年。
很動人,是吧?
我不知道該有什麼結論。寫到後來我漸漸看不清事件或餘生,看不清泰雅族人的高山峻嶺美麗的臉,看不清矯健的身形高挺的奶子或圓臀,四周開始瀰漫小米酒與摻了一堆什麼的各種維士比的酒氣小雜鍋的菜肉香與愛人初初開始腐化時,些微的甜臭;四周手手腳腳都在舞蹈或奔走或拉弓或交纏殘影幢幢,血,及頭顱圓睜的眼…
我仍想望著許多年前未開發的山巔水湄即使沒有步道沒有水煮蛋區,想望獵人在草野叢林間獵獸的敏捷與氣勢、祭典裡的酒與舞,而失去原鄉的書寫或記錄,多麼令人悵然。
餘生。
【其他書的連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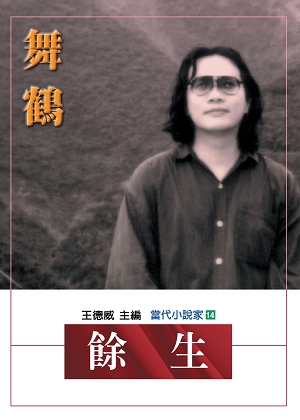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